更小的世界
该收收心了,暑假要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暑假要结束了,准确地说,是5年11个月23天,自2014年6月9日起,到2020年5月31日。
这是个忧伤的比喻。大概意思是说,当我不再是个做题家,就没正事可做了。但我的确这么认为。总有人告诉我,应该划分出明确的区域,工作和生活应该各自区分出来。不过,我始终无法理解“生活”算是个什么概念——为什么人一定要把生命中的一半设定为痛苦,再把另一半设定为快乐呢?仿佛人是为了痛苦而活着的一样。这或许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良性的负反馈循环,但总的来说,对我而言,这个结论很荒谬,我不接受。
活着的每一秒都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感受是什么,我知道定义的定义是什么。
来,讲讲,在疫情之前的半年,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吧。我每天八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背着书包离开三斋,在楼下的超市里买份面包牛奶。前往理化楼229房间,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查看前一天的计算数据,等一等师兄到来,问问他下一步该如何操作。中午到了,穿过图书馆,进入食堂,返程。下午三点,铃响,去游泳馆,晚饭,继续在实验室挂机,看看文献,当然,更多时候是在和群里朋友们扯皮。归还,躺在床上看一集动画片。有一些小细节:我会注意在起床后把排插上插着的充电宝放到包里,换上另一台充电宝充上电;我比较腼腆,不怎么和师兄他们一起吃,我会自己对吃什么进行选择,是去北侧的小吃铺,还是去食堂,或是来一顿叔叔家的汉堡;七点十分手机游戏的定时活动会响铃。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这就是我,一台在一幢十五层的高居民楼、四层楼老教学楼的与几间平房之间徘徊,循环着休眠、对着键盘敲打和寻觅食物等几个行为的自动机。
疫情的这半年来,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变成了另一型号的机器,多数情况下,活动范围不超过方圆20米。我醒来,我进食,我对着一个大型显示器“哈哈哈”,我对着一个中型显示器“哈哈哈”,我对着一个小型显示器“哈哈哈”,我沐浴,我休眠。
这是定义,最科学的那种。
当然了,有些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那种和人建立起了联系的幻觉。让我勉为其难地认可:每个人的生活都没什么不同,人也可以认为生活没什么不同,生活也可以没什么不同——就像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样,日子可以不用焦虑的,自然而然的,觉得一切都没什么不同的心态。生活中存在着被称为“锚点”的东西,它可能是爱人的容颜,明星的活动,甚至是手机游戏里的日常任务。只要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这群驴绕着那根柱子转。
多亏这些幽闭的日子,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看问题的视角。视角是很重要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的视野都是很狭窄的,同一段时间内只能思考并做成一件事。不知不觉中,我们就被它定义了,甚至还以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自己,有着天然的合法性。
我不喜欢被人玩弄。所以,我能理解这种绕着锚点打转的情结,但我不接受,至少要保留意见。
多少还是存在有让人惦记的念想的。那更大的世界——
小时候我一直觉得,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是科学家,人生最重要的事是追求真理。科学家很聪明,什么都懂,为人风度翩翩,素质很高。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正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陈景润那样的,思绪全部沉浸在一两个犄角旮旯里,其余的生活自理能力为零;能像钟南山一样文武双全(字面意义上)的人极少。即便是生活体面的高校教师,其中大多也不过是个自己研究领域中的论文搬砖工而已。平庸的理工科教师也许还对推动生产力发展有极小的作用,而文史教师则大多只是为西方那一套或中共神学布道的马前卒。他们日子过得好,看似光鲜,并非因为他们很厉害,只是因为他们在那儿罢了。
我扫视了一番。我,我的同学,师兄师姐,我的导师,我同学的导师,顶级宗师。所有人从天而降,坠落在无垠的空间里,我的视野中绘制出一幅由地位作为Z轴构成的,山峦起伏的三维地形图(landscapes),绿树花香和枯枝烂叶,崇山峻岭和荒山野岭。我明白了,在那儿的方法有两个。要么做一个开了外挂的大老板,占山为王,你让人恐惧,你就是真理,谁上来都得先被不讲道理地剥下几层皮来,反正他们也举报不动,没人管事;或者也可以做一个凭直觉吃鸡的大神,指哪打哪,你确实弹无虚发,为人敬佩。
但是,一个极端到只能专精做好一件事的人,真的是强者吗?对社会来说,他也许是有用的;可对个人来说,他永远被隐秘的欲望折磨着:随着对熟悉生活的沉溺,一切的未知都会让他感到不安。很多人即便得到了力量,也没有得到救赎。以我了解的例子说,就算是北大的教授也会相信练气功,季老师当时和我说“你就把他这样当作是相信过世的亲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好了”。
我很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偏执,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在这里做这个而存在的。在超前沿地带,庸夫怎么才能同没有感情的怪物和不顾他人的疯子竞争?
从儿时起,我们就被教育要仰望星空,认识更大的世界。读更多的书,学习更多的知识,似乎是奔向这一目标的正道。但读再多的《十万个为什么》也不能让你造出芯片,K12的过程中拿再高的分也没法打赢贸易战。这些都不过是大人们的夸奖,夸奖并非完全来自于人的真心,更多来自于体制的既定答案,它是狭隘的。我们不过在这一阶段里被驯化成了优质的模式匹配自动机,这就是我们。
最喜欢为高考和通识教育鸣不平的人是杀入了名校的做题家本科生。可你将知晓真相,而真相让人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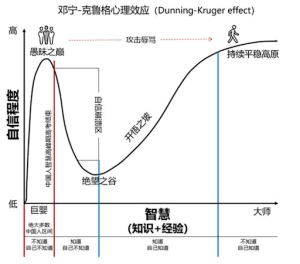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最终一定会成为某种工种的专才。即便是从事以掌握真理为基石的职业,除了费曼朗道之类少数的几个能融会贯通多个领域的大师,多数人也只能掌握最前沿的那一点冒头的内容,靠在上面折腾骗经费过活。事实上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得不到更大的世界,我们得到的是更小的世界。想要说服自己正在体会更大的世界,需要一点欺骗感受的谎言做支撑。
那就退而求其次吧,专才能拿钱,拿钱去消费,自由的资本带来自由的选择。大家都在这么做,我这么做肯定也没错。
该做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工作只是工作,我要攒钱去旅游,看看更大的世界”,于是它变成了一种资本的输出终端:在难得的喘息之机中,每个假期都被出行计划排满,或是在拥堵的高速路上左右冲杀,或是伴着夜色红着眼登上飞机,啊,多么精致而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
倒不是说死宅就比现充高级,我也是愿意呼吸新鲜空气的。我只是在想,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呢?我走进一个长条状的大屋子里,在这个屋子里坐下,三个小时后,走出这个屋子。哇嗷,我来到了另一个国家,冒险开始了!理性告诉我,我穿越了半个地球,来到了另一片大陆,这个景点有千年历史,那家餐厅值得一去,这都是计划好的,旅游公司是大品牌,完全没问题。
但很不幸,另一层理性告诉我,我的确只是在一个长条状的屋子里坐了三个小时,再走出去,遇到了几个我平时不多见的,其他肤色和瞳色的人类,漫长的行进后,我进入了一幢建筑物,把手里的几张纸交给同样样貌的人,一段时间后,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些热气腾腾的食物。尽管我可以把这一切包装起来,描述为“我乘坐飞机去了×国,在××餐厅吃了顿饭。”但这仍不能消解我对体验的疑虑:国家、景点、餐厅……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他们在我的脑海中实际上只是一个符号,即便它们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对他们的了解也并没有比在照片上看到时增加多少。我对旅游中所有目标的理解都只来自于信息载体上的文字和图像,而非长久生活的直观体验,又或者说,我的认知被塑造死了,我早就失去用感受和直觉来认识它们的能力了。我也许只是在执行一个早就被前人设计体验过无数次的,被计划好的程序,一个事先让我觉得这一切有价值,然后再依次实行的流程。
不,我不是想重复什么“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之类的屁话。地球的确已经快被开发殆尽了,WiFi信号卫星都要上天了,不去殖民火星和半人马座α星的话,未来的世界怎么内卷都不过分。社会肯定还是要进步的,搞这种反动主义只会伤人害己。我想说的是,以旅游为代表的消费真的能让人见识到更大的世界吗?我们真的喜欢把探索“更大的世界”当作人生的愿望之一吗?我们真的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吗?
视角是很重要的,而我们的视角早就被入侵了。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处拍照就能为世界的观测者了吗?
请回答社会学研究的终极问题: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是有用的吗?
快想起来,想起来自己到底为什么快乐吧。
我迄今为止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发生在初中。那时,我有着用不完的劲儿去做所有事情。在学校能学进去,考高分,所有的课余时间也都有事情做,写作,画画,追番,关心时政,追逐着那几个操弄着西方话语的知识分子发表的时评,玩最新的游戏。我文体两开花。我在各个方面都有好事做。我知道这些都是有趣的事情。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男孩子中还是女孩子中,我穿梭在各个领域里,只分别把一个触头伸出去接入其中去感知,享受着这份孤独的探索,忘记了与生俱来的那份疏离感(alienation),以为自己迈向了一个个更大更先进的,别人不了解的世界。
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渺小与狭隘,还不知道任何工作都需要做成到一定水平才具备社会意义上的交换价值。无需多余的咒语,我自己就是那个欺骗感受的谎言。我以为我与这个世界建立起了真正的联系。
人嘛,大概在无拘无束的时候才觉得开心比较重要,可是开心容易,而无拘无束很难。
现在,衡量世界的大小,与之建立起联系的唯一方式变成了资本。超越了童年同温层的生活环境后,在更宽广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确是没太多可以互相理解的地方的,反而是资本让大家连接在了一起,有了一个社会共识。
但这种连接终究是虚假的。对多数人来说,它只能是一种真正了解彼此之前互相试探的小工具(沟通协议已启动:今年的网红情人节礼物准备好了吗?)。真实的连接在于后面的功夫。能够靠资本真实连接彼此的人只有那些大家叫得上名字的,在新闻头条上打着明牌的大佬。以体制作为故事背景的主人公注定只能有那么几个,普通人怎能有自信在这里不幸地共情呢?
无数条平行线出现在我身旁。我从小到大的同学们,身边的长辈们,还有网友和租房打工的凤凰男女同事们。故作坚强的一颦一笑化作向外扩散的情报节点,振动着,流露出关于愿望的信息形态特征。不同出身的人们带着各自的祈愿,前往都市的战场刀口舔血。我看到了。这是他们的幻觉,虚假广告罢了。你们都知道自己会输,但是你们还活在“要赢”的幻想中。这是因为你们不想忘记,对吧?你们需要它,你们需要热情,需要这份虚假的希望。谎言已经揭晓了,但你们不能接受,你们一直生活在其中,它就是你们。
Little do ye know your own blessedness; for to travel hopefully is a better thing than to arrive, and the true success is to labour.
发现问题了吗?
精神稳定的普适条件并不是足够积极上进并取得正反馈——那是高手的玩法——而是逃避。对多数人来说,世界足够小就可以了。只要和象棋冠军打拳击,和拳击冠军下象棋,总有赢的机会,总能处在自我感觉良好的高地上。
人总归是要溺死的。
我感知,我理解,我体验,我顺从,我清楚。只是,一点小小的坚持:我不喜欢被人玩弄,最好能把它们都揭露出来,有一点是一点。
视角,视角,视角是很重要的。无论在哪里,用自己的视角去体会,然后,跳出来。俯瞰。超越它们。
死也要死个明白。
我终于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生命中唯一有价值的进步是:即使叙事惨遭来自其他世界的解构,也能获得在无意义中前进的勇气。超越(transcendence)就是转变(transformation)。
摧毁锚点吧,然后在下个新世界抛锚。
你会明白孤独。
三个世纪在太空深处孤独的漂流,在异世界那难以想象的人生旅程,身体和灵魂注定要经历的无数磨难和考验,在他的身上都没有丝毫痕迹,只留下成熟,充满阳光的成熟,像他身后金黄的麦子。
云天明是生活的胜利者。
六年来的红药丸:更大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一旦与世界真正地建立起联系,这种自恋的幻觉就被会立刻移除。事实上的逼仄将会与心灵的解脱交映,你很难说这是好是坏。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理应明白要爱真实的人胜过抽象的人,要爱具体的劳作胜过虚妄的成功。你的最后一个无意义之夏结束了。
极端的理论才有生命力。选一个吧。
你知道敌人在哪一边。
2020年6月25日 初稿
2020年9月6日 二稿